春日泥土与青草的芳香
勾起回忆中那恬然的微笑
于是她转身继续向前走
任由露水打湿裤脚
黍并不会经常想起神农。
长久而固执地去记忆某人某事,有时或许是出于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,譬如老天师带了那么多学生出来,却独独把自己的笛子赠与了学生的后代小满;有时或许是出于一种告诫自己不可忘记的责任心,譬如——黍正准备离开时,瞥见远处的房间里还有一捧幽暗的光亮。她走过去,敲了敲门便推开,问:“左公子?”
房间里的人正是左乐。他脱下了晨间在田垄地头干活的装束,重新换上官服,似乎正伏在案前誊抄着什么,闻声抬头:“啊,黍小姐……”他瞥了眼自己面前几张薄纸,连忙道,“黍小姐先行离开就好,走之前我会熄掉灯的。”
黍略略点头,“左公子不用着急,只是夜间还是多多注意安全。”她本打算转身,却在瞥见左乐案上的纸张样式时顿住身子,纠结片刻,问道:“左公子在誊抄的是……”
“是千年前神农躬耕于此时,所亲手撰写的《农荒记述》。”和她料想的相反,左乐没有隐瞒,而是将那些薄纸展开给她看。黍盯着那几张纸——纸本就单薄,而左乐手中的那些在浸泡了经年的岁月之后,泛黄变脆,若不小心些,似乎就要四散开来,化作飞灰随风而去,竟让人无端端想起“脆弱”一词。
《农荒记述》在炎国早就雕印发行,如今已不知再版过多少次,若要是由小满和禾生得知,定是要问左乐为何要去抄录一本家喻户晓的书,去做那劳什子无用功。但黍没有问。她自然知道左乐真正在誊抄的究竟是什么,不仅仅因为她自己在漫长的光阴里就翻阅过无数次《农荒记述》,当年神农写作这本书时,她甚至就坐在她的身旁。神农写作,她则翻看那些神农带来的书籍,从农术记载到市井小说,不一而足,彼时炎国的书还是线装,她翻阅的动作得放轻些,差不多得是神农为她编发时拈过她几缕发丝的力度。黍想起来,她本是打算在那个冬天把它们看完,打发夜晚的时间。
《农荒记述》起初并不是一本专门记录农业技术的典籍,至少神农在写作时,可没打算完全把它当成一部志述农术的书来写。神农一直以来就有记日记的习惯,晚上房间的窗户半开,幽幽的清风吹进来,她与黍闲谈着各种各样的话题,关于新来的几个学生,关于乡亲们,关于今年的收成,关于大荒,然后把它们通通诉诸笔端。人的记忆是不牢靠的东西,神农告诉她,那些与黍的对谈和劳作,不快些记下来,自己就会在某日的睡梦间不慎放任它们如同袅袅升起的炊烟般散去。
梦么?黍故意不去搭理神农那些关于遗忘的说辞,只是笑着问,我们的神农会梦到些什么呢?
神农不语,眼神往旁边瞟,黍仍然笑吟吟看着她,片刻后神农无奈地叹气,嘴角勾起了一个黍所熟悉的弧度,延伸出来几道皱纹。梦到了你和绩。她说,大荒城的春天到了,路上结的冰融化成水,土里开出来的花颜色也和洗过一样鲜艳……梦里绩还在大荒城,他在织一方锦缎,虽然还未完工,但在我看来那已经是堪比尚蜀锦绣的作品啦。你呢,你在地里头,禾苗长得高高的,你坐在里面,从外边看过去,几乎整个人被掩住。说罢她笑得更深,哎,要是真的就好了。
那你呢?黍问。
我在给你编花环。神农说,不像在描述梦境,反倒像是陷入了某种渺远的回忆。她说,我记不得手里拿的是什么花了,也记不得那花环是什么模样,但我记得是在给你编。好像已经完成大半了,但这个时候已到卯时,我就醒了。
这句话音落下来时,神农手中的笔也搁在了一旁。黍探身去看,最后一张纸,短短三十八行,工工整整的方块字,记的不是她们口中那些缥缈的梦,而是大荒节气,农耕桑麻,事无巨细。所有手稿累起来,竟然已经有了厚厚的一摞,黍看着从案上堆起,直到神农下巴的书稿,问她,什么时候出发?
过几天,天晴的时候。神农说。
这回轮到黍陷入沉默。神农轻轻握住她搁在桌上的手,打趣她,刚刚还埋汰我,我以为你早就接受了。黍横了她一眼,却没把她的手挥开,说,接受当然是接受了,不接受还能怎么办?我只还是觉得,……可惜罢了。
对不起啊,黍。神农轻轻说,惹你不高兴,可到头来,也没什么能赔给你的东西。
我还能要你什么东西……你给我的已经够多了。
神农摇摇头,不能这么说。她说着,突然双眼一亮,竟然如同一个孩童般提议,那不如,我回来之后给你编花环吧。
花环?黍愣了一下,也不自觉地笑起来,你做的那个梦吗?好啊,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?
等我回来吧。神农说,双眼弯弯,等我从北边回来,就给你编花环。我前几天给你别的那朵花,你还戴着呢,这次你想要什么花呢?婆婆纳和你发尾的颜色很般配,不过它太小了,要一团一团地编。稻花怎么样?它也很小,但是我有办法。或者你自己有什么想法,等我回来之后告诉我。那时候大荒城应当正好丰收,而不像现在这样是早春了吧?正是欢庆的时候……大家还有很多很多时间。
——对了,黍。你呢?你也会做梦吗?
——倒也不是没有,只是不常做罢了。说完她顿了顿,便转向下一个话题。
后来神农从北方带回了那一粒被诅咒的种子,而她也离开了。她离开之后,黍把那些曾经放在她们两人之间,所记述的那一切整理成册,司岁台又摘去了其中关于岁的片段,遵从了神农生前的意志,将其命名为《农荒记述》,雕印出版,自然给黍也送了一本过来。黍第一次翻开它时,却觉得有些陌生:这上面记录的,真的是那些她们在无数个夜晚交谈的东西吗?可再定睛一看,无疑是的,除了有关岁的部分,剩下的内容没什么变化,只是校对了一些偶然出现的病句与错字,她感到陌生,是因为她已经太久没和神农闲聊过。
那天晚上黍难得做了一次梦。故人没有入梦来,她梦到的是另一番景象。大荒城丰收,比过往任何一年的收成都要多,举办了最为隆重的神农祭,她的学生笑着对她说,老师,我们真的做到了!能够抵抗天灾与源石的禾苗,我们终于研发出来了!真的吗?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吗?来不及思考其中的合理性,她便被梦里大荒城的气氛和学生的情绪感染,不由自主地露出笑容,刚要说些什么,学生便说,她如果能够知道,一定会为我们自豪的。她?黍愣了一下。神农呀。学生说,神农她也一定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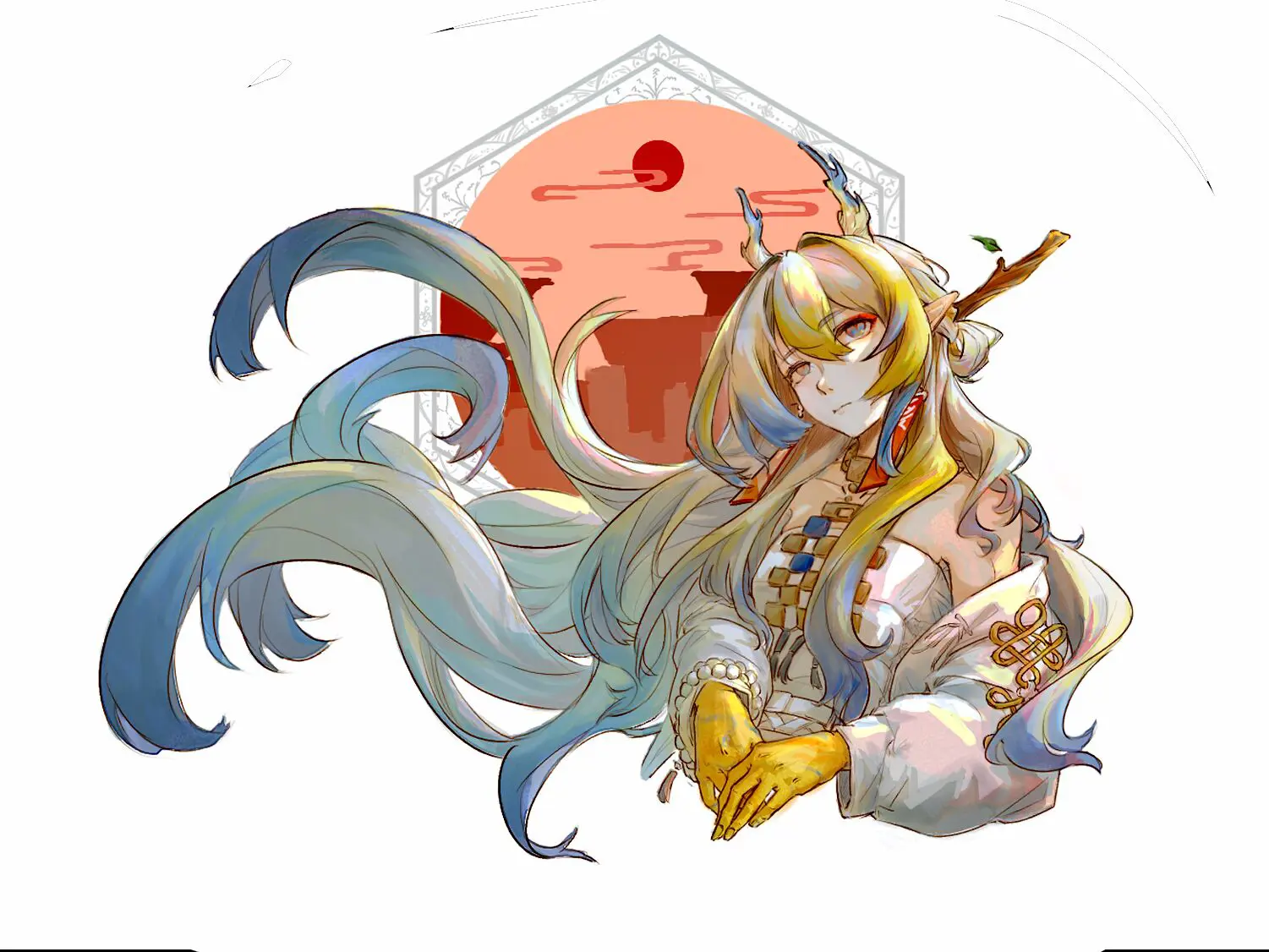
话说到此黍便醒来。她没有放任自己愣神太长时间,收拾收拾便出了门。秋日里,和神农说得分毫不差,虽然比不上梦中那般,但这一年仍然是丰收的一年,没碰上天灾,也没出什么意外,一派金灿灿、喜洋洋,热热闹闹的景象。神农离开的那一年,曾经有人提出取消当年的丰收庙会,来纪念她的牺牲,但黍极力反对,说那个人绝对不会愿意大家这么做,所以庙会在当天晚上还是如期举办了。在过去,她们从来都是一起来逛庙会,各式各样的河灯在摊上一排排陈列开来,神农俯身挑拣,她们再各自提着那些灯,将它们放进河流里,目送它们远去,最终化作河流远处一盏小小的、小小的光。彼时她还在为神农提出要离开而怄气,神农安抚她,指着那盏灯说,人终有一死,我是走得越来越远了……不过,黍,我会一直在这里的。
在那之后,每一天都是循环往复的希望与失望,但不管她感到有多麻木,不管绩与她争执过多少次,她都没有绝望过,那是她们之间的承诺,也是她从神农身上学来的一课。她又想到:老天师来找小满,将笛子交给小满,是出于某种师徒情谊一般的感情;左乐在深夜伏案誊抄《农荒记述》,大半是由于他身为秉烛人的责任心,那么,她长久以来惦念着千年前的她,大荒的子民们世世代代传颂着她,是出于什么呢?黍是清楚的。那是一种被各类各样的思绪与离愁包裹起来的,难以言明的东西,用任何一种单一的词汇去形容,恐怕都不够准确。这也没有办法,不是什么都能像实验室里天师们测算的结果,能被用数字精准量化。
左公子。她突然问,前两日的神农祭庙会,有去看看吗?
“有。”左乐说,“我听了祭祀神农的戏,禾生跟我解释了很多。我那时以为……”他有些尴尬地撇开眼神,用手挡着嘴咳了两下,“咳,抱歉,黍小姐……我那时以为‘神农’仅有一人。直到我得到机会,誊抄这部《农荒记述》,方才得以勘误。”
“没什么。”黍轻声说,“她已经是故去多年之人,又有什么人还能记得当年这一段事。左公子愿意去翻这些陈年旧事,或许于她也是件慰藉。”
烛火摇曳着,左乐的面容却很清晰,“黍小姐过誉。补足这一段记述,也是为了供司岁台同仁参详,是我的本分。”
黍微微弯了弯嘴角:“不过当年将那些段落摘去的,也是司岁台。”
左乐刚想开口解释什么,碰触到黍眼神中的笑意,便也心领神会,于是转而说:“不过那一位神农,她自己也一定……”
左乐的话并没有说完,但黍知道他想要说什么。她轻轻摇头,又嘱咐了左乐几句,便转身向屋外走去。初夏还不算炎热,夜晚的大荒城带着些许凉意,风轻轻吹来,撩开她鬓边的发丝,仿佛熟人在低着头和她亲密地低语。不,她不会知道了。黍沉默着想,那个人早就在千年前去世,而她种下的种子,却又让黍每一年都疲惫不堪,然而又无可奈何地想起她。她抬起头,夜风仍然轻轻地飘荡,给她送来了春日泥土与青草的芳香,她知道等到第二天的清晨,她再路过田间时,会看到那一条河流之上,飘着淡淡的薄雾,淡色几乎透明,却又隐隐约约显出一点白来。隔着薄雾她会恍惚看到神农正站在对岸,怀抱着那一筐谷物,向她勾起一个她再熟悉不过的,恬然的微笑。然后她转身,平静地继续向前走,露水从小径两旁的草叶上落下,打湿了她的裤脚。
(责任编辑:广英和荣耀;网页排版:Baka632;绘图:猫猫我摸)